【北大政管学科建设】——【青年学者专栏新书发布】封凯栋副教授出版英文专著《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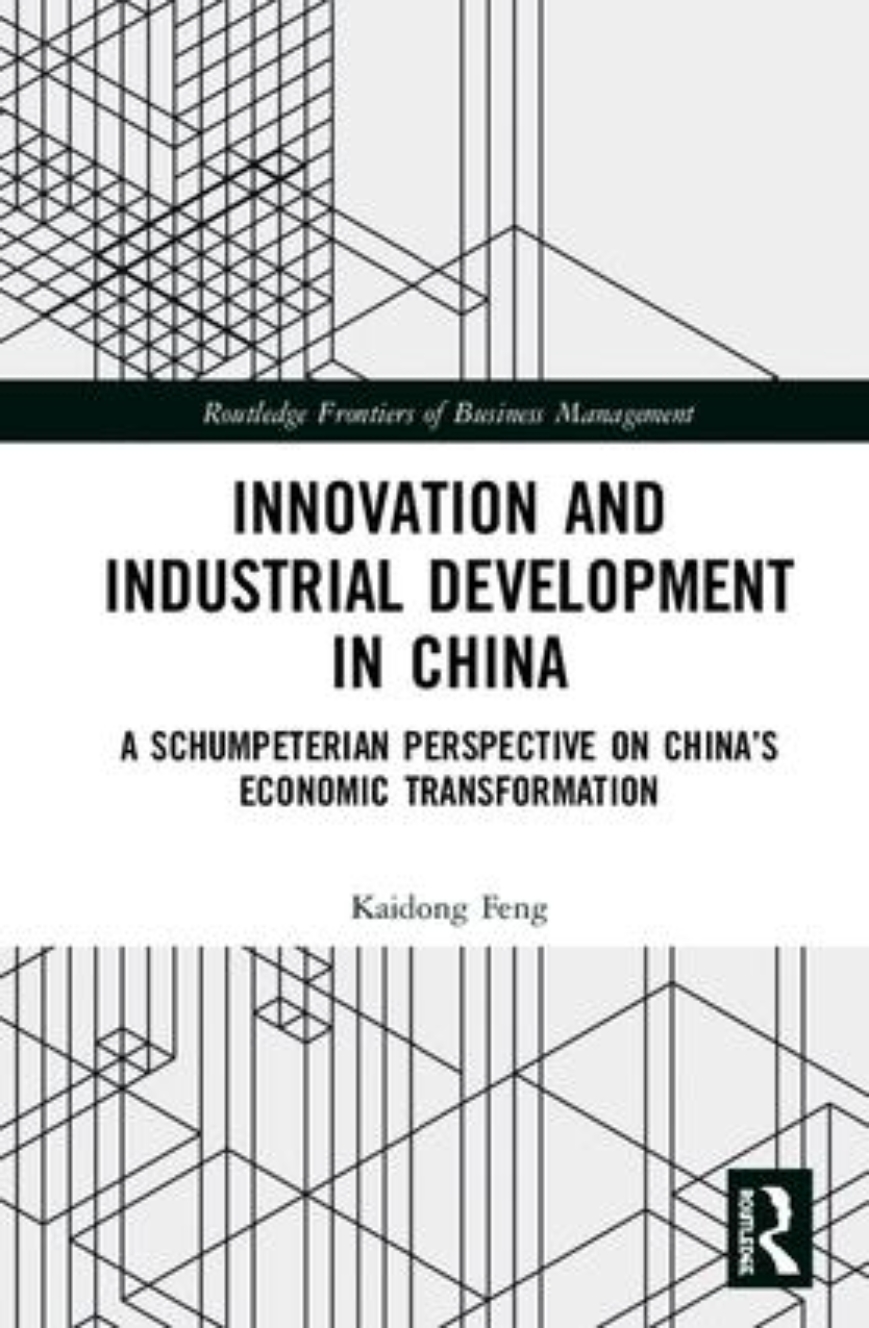
【学者简介】

封凯栋,男,政治经济学博士,英国(正版)365官方网站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本土的创新企业是怎么崛起的?”
“中国工业由‘世界加工厂’向‘自主创新’的范式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如何解释中国工业化历程中的能力跃迁?”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这本著作将尝试回答以上问题。该书为我校封凯栋副教授独著,2019年9月由Routledge出版社最新出版。其内容浓缩了作者自2003年至今15年以来对中国工业实践所做的发展性的研究及观点,也呈现了作者历次参与中国具体政策讨论、推动政策转型的基本认识。
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面临关键转型的重要时期,本书力图系统地诠释中国工业自主创新得以萌生与发展的源动力,以为工业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梳理经验教训,为学界同行开拓讨论空间,同时,反击西方以特朗普政府为首的评论者们污蔑中国创新主要依靠偷窃西方技术的谬论。
写作的两个目标
本书主要有两个目标。目标之一,是通过研究中国工业的发展实践来解释中国创新型企业的崛起。作者通过回顾中国工业自1980年代以来的两次重要转型来分析其曾经遭遇的困境和崛起的过程。本书强调,本土创新型企业崛起的关键是塑造了新的企业内部组织系统,尤其是以工程师群体在企业内影响力重新崛起这一现象为代表的企业组织内向型战略控制模式的产生,推动了本土创新型企业的形成;同时,在现阶段,本土创新型企业模式在企业与产业间的扩散势必会在更大范围内给中国工业持续带来变化;且这种变化的趋势甚至不会受到外界国际贸易冲突的干扰。由此,中国工业整体的创新转型将具备其内在生命力。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点的重要性,那么解释这一模式为何曾经不是主流,以及这一模式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就成为了重要任务;这也构成了本书的第一个写作任务。
本书的目标之二,是推动发展中国家“赶超式发展(catching-up study)”研究的发展,尤其是与作品所依托的“技术学习范式(assimilation theory)”的经典理论进行对话。本书挑战了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工业化可以通过本土企业对成熟制造经验的积累发展而获得的传统思路(即下文所指的“逆产品生命周期”的经验积累);强调后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关键的能力跃迁,只能由超越短期经济理性的战略决策,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和技术学习系统来驱动。而在中国过去40年的实践中,这一角色是由本土创新型企业来扮演。由此,发展中国家本土工业技术能力的崛起,尤其是从劳动密集型阶段向开发型、创新型?阶段的转型,不可能依靠遵循已有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开展相应的生产组装活动形成的经验增长来完成,而是必须依靠本土内生的战略意志及相应的技术开发与技术学习实践来驱动。要解释这一现象,评论家们工作的重点就不应该仅仅是对成功的赶超发展经验进行概貌性、阶段性地刻画,而是要在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上解释驱动结构性跃迁的政治经济过程。本书尝试通过两个工业在中国40年的变迁来分析这一点。
主要内容
本书以中国汽车工业和电信设备工业在过去40年的发展为案例分析对象,藉由详实的档案记录和对数百位受访人的深入访谈为素材,通过解释上述两类工业中关键企业的兴衰,来分析中国工业自1980年代以来的两次结构性转型。
本书分析的第一次结构性转型是始于1980年代初期的“市场换技术”政策实践。本书用前半部分篇幅解释了“市场换技术”这一政策范式是如何从1970年代末所遭遇的重大困难中被改革的先驱者们摸索出来,并在1980年代初开始被推行的。作为推动本土工业发展的政策举措,“市场换技术”的设计者们曾赋予技术进步和发展生产以明确的战略目标,部分产业领导人甚至还制定了实现各阶段目标的时间表。但在一系列重要的合作项目中,由于面临着外汇短缺、技术能力弱、对在复杂工业中发展技术能力的规律性认识不足,以及国内各利益相关者目标不一致等问题,中方在拥有技术优势且战略目标明确的外方合作者面前往往落于被动;这使得外方得以转换合作目标(放弃了技术开发性的内容)、重置实践中的合作议程。在大部分“市场换技术”合资企业案例中,由于外方在事实上主导了具体的战略过程和组织过程,使得它们得以逐步重塑中国企业的组织系统,肢解了其开发体系,使其服务于外方自身的全球布局,即将中国企业改造为其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制造厂。
当然,这一转变的产生还与国内企业的改革序列和思潮存在紧密的关联。企业治理改革中一度以承包人、股权为中心的调整,使得当时的中国企业更强调资源配置权向上集中,而难以实现广泛的组织动员来驱动内生的技术学习,因此更倾向于接受跨国公司对企业组织的重塑。本书在第六章讨论了这一问题。
“市场换技术”实践在实现技术进步目标上的一系列失败陆续改变了政策实践的初衷。伴随着国有企业持续遭遇困难和大量企业的管理权产生震荡和下放,这一政策范式在技术学习方面的初衷陆续被淡忘和边缘化。无论在1990年代大批国内企业涌进中外合资浪潮的时期,还是随着加入WTO之后资源约束不再是国内企业的瓶颈时期,相应的工业实践都没有再回到“市场换技术”范式的制定者们最初设计的道路上,而是走向了利用国外成型的产品和技术、发挥本土的劳动力优势来快速拓展产能的方向。
由此,“市场换技术”的结构性转型虽然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铺平了道路,但它也使得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放弃了原有的技术和产品,在技术上陷入了对国外合作者的过度依赖。也就是说,大量的中国本土企业被从计划经济“五定五保”体制下的生产工厂释放了出来,但没有转变为在产品与技术决策上完全自主的创新型企业,却成为了跨国价值链条中的加工制造工厂。
本书分析的第二次结构转型是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创新型企业的兴起。在汽车和电信设备工业内,本书研究了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和哈飞、华晨、奇瑞、吉利、比亚迪等两代本土创新型企业。它们最初都崛起于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外,由此并未被纳入“市场换技术”范畴。这使得它们一开始就需要在不利的资源条件和政策条件下竞争谋生存,但反过来又使得它们不受当时的主导范式约束而自我尝试。由此,这些企业一方面由于受到起步初期的资源约束,倾向于从本土已有积累和传统中汲取养分、扎根于中国基层市场;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受管束”,敢于突破全球价值链的层级体系,主动在全球范畴内开放搜索并整合技术资源,最后它们演进出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征的系统性整合创新模式来。
本土创新型企业的突出意义不在于创制了先进的技术,而在于为国内工业提供了新的企业组织系统的范本:这种组织针对技术学习,尤其是针对产品开发与复杂技术开发任务而言是行之有效的。这种组织形态具体表现为本土工程师群体在企业组织内的技术学习系统中的重新崛起,其实质是要求以内生的、分散化的决策来实现对与技术学习活动紧密相关的组织成员的充分动员,从而实现自主战略意志与有效的技术学习活动的双向互动。与大量西方评论家臆测中国本土的创新型企业是靠政府的扶持而发展起来的观点不同,事实上,创新型企业在诞生之初都面临极其不利的资源条件和政策条件;然而,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条件正是这些企业驱动自身组织系统转变的关键原因。在战略意志与执行技术学习的组织系统形成耦合后,这批企业在国家的改革开放中抓住了国内和国外多种技术资源,持续地投入自己有限但持续增长的战略性资源,通过在国内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开拓新的市场空间而得以萌芽与发展。当然,这些创新型企业并不是一喊“自主创新”的口号就成功的,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遭遇了巨大的困难:第一代先驱企业普遍都遭遇了失败;但后来的企业通过吸收并发展相关经验,顽强生存并发展了起来。
本土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触发了人们对“市场换技术”范式的再思考,促进了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的变化,最终推动了中国在2005年面向“自主创新”的政策范式转型,以及“市场换技术”主导范式地位的终结。这一转型为中国工业创新能力的逐步提升铺平了道路,开启了后续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强调创新转型、颁布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战略举措的新时期,以至于被特朗普政府认定为是对美国创新经济霸权的威胁。
对于学界同行而言,本书的研究挑战了传统观点,即认为通过遵循“逆产品生命周期”的经验积累会自动推进发展中国家工业能力建设。要想探索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跃迁问题,人们就必须关注工业活动的组织化、制度化过程中的控制权问题,这样才能深入探索企业技术学习活动中的战略承诺和资源配置决策。如果欠缺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回答,那么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创新型企业崛起和国家持续工业化而言,目前的激励制度、所有权问题或是学习型组织、开放式创新等流行理论都远不能提供足够的解释力。
本书特点
本书采用了熊彼特主义的范式,其分析的重点在于不同企业的组织系统,以及宏观政策给这些组织系统所带来的影响。为实现这一目标,本书以作者自2003年以来针对包括企业管理者、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政策决策者和专业科研人员等相关人士大约500次的访谈作为素材和基础;同时,这些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我校路风教授领导的关于中国自主创新研究的组成部分;此外还曾得到国家科技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支持。可以说,本书所扎根的研究工作本身就是作者参与推动中国工业面向“自主创新”政策范式转型的论战工作的一部分。
阅读次数: